十幾輪的面見已然讓聖女失去了耐心,其實昨日的聖祭早已令她疲憊不堪,但高坐上首的她仍然得維持端正坐態,實則不斷想著是否太過急躁,做出了草率的決定。
但她已有了與她交換身分的適合人選,而今日她這般大動作,驚動了宮中那些貴人,若沒能行動,恐怕之後再也沒機會了。
她身在水塘,不甘一人陷溺,只能用這樣卑劣的方法,拖著其他人下水,做她的替死鬼。
又一位無辜的姑娘走進內殿,她抬起頭看,是夢中鏡裡的面容。
狂喜、愧疚在同一個瞬間湧上心頭,從來都是冷靜端莊的聖女,在僅有兩人的內殿,難掩失態,激動地站了起來。
女孩的身形依舊纖瘦,只是那雙眸子今日似乎染上了不同的色彩,反倒令她們倆更加相像了,她緩緩步下台階,一隻手掀開掩面的紗巾。
「啊!」女孩瞪大了雙眼,方才她站起身來都沒有顯得多訝異,現下卻明顯吃了一驚。
「我們很像吧?」
雖然家中沒有鏡子,但是女孩卻曾在洗衣時藉著水影來看清自己的模樣。
「是……」聖女問話,女孩不敢不答,卻在心中想:原來我們生得這般像,但一個是高高在上的聖女,一個卻是卑微到地裡去的平民。
命運竟是這般不公平。
似乎是看出女孩在想什麼,她聽到自己問:「很不公平,對吧?」就像是引誘著迷途的羔羊一樣。
女孩震驚過後,這次卻不敢回答了,不公平又如何呢?這個世間本就是不公平的,只不過聖女是享受天上偏愛的那一方罷了。
「你可願意與我交換身分?」她不想等待了,時間不多,她還得說明許多細節才行。
女孩沒想到自己會聽到這句話,愣在原地,她繼續道:「我知道這些話聽在你耳裡很荒謬,但我不想再做這個聖女了,只有你能夠代替我。」
女孩終於反應過來,急忙跪下:「我?!聖女殿下,我、我一介民女,怎麼可能代替您呢!」
「這聖女誰來做都沒有區別的。」女孩還未來得及反應這句話的意思,就被她搶白:「你與我長得如此相像,若連你都不行,就沒有人能行了。」
「可、這,您為何不想當聖女呢?」女孩大著膽子問了出來。
她看得出女孩腦海裡有太多疑問,為什麼她要放棄聖女這樣常人眼中尊貴不凡的身分,寧願到民間當個受人蹉跎的民女呢?
但是她不能說。
她卑劣骯髒,從前這一切是她獨有的絕望,如今卻要將砒霜包裹成蜜糖,裝作誠意十足地雙手奉上。
「我只問你,你想做這個聖女嗎?」她盯著女孩的雙眼,像是在照鏡子,她似乎看到了早晨夢中的情景,一雙雙手印即將模糊鏡中人的面容。
女孩沒有沈默太久,低聲道:「沒有人不想當聖女的。」
「包括你嗎?」
女孩沒有回答,但是她已經知道了答案,卻並沒有多少如釋重負的感覺,這一刻,某個部分的她被判處了死刑。
「那聖女殿下該怎麼辦呢?」
「我會先回到你家中,再找藉口搬走。」
「我家裡很窮的,聖女您可能吃不飽也穿不暖,您想要自由,可……若無法吃飽穿暖,又談何自由呢?」
「這你不用擔心,我只會待幾天,之後便找機會遷居。」
她明白,這對女孩而言誘惑實在太大了,她也是。
如同石牆縫隙生出的嫩芽,見到了一點陽光,便掙扎著、不惜扭曲自己的形狀,也要將身體延展出去,求得溫暖。
她們很像。
她聽見女孩啞著嗓回答:「好。」
她與女孩講起她宮中的生活,講出口才發現她的日子乏善可陳,除了巨大的悲哀籠罩著她,剩下的全都不值一提。
給予女孩的叮囑裡,唯一真實的就是那份悲哀,但她只能說謊。
「你過得快樂嗎?」她問,她希望女孩至少曾經快樂過,雖然她並不祈求交換身分之後,能夠擁有那份快樂。
女孩還是不太敢看她,低垂著頭道:「我過得很快樂,除了窮了點以外就沒什麼煩惱了。」說到這裡女孩笑了一下。
「抬起頭吧,出了這個門,你就是聖女殿下了。」
她望著身穿華服的女孩,不知道為何,兩人都紅了眼眶。
—
同樣的轆轆車輪聲,相較於前往聖殿時,要平穩得多,華麗的車架,一旁小心翼翼服侍的侍從,這是她從前想都不敢想的畫面。
她成了聖女,高高在上的聖女。
昨日的她仰望車架,為了能見到聖女一面引頸盼望,今日的她就在車架裡頭,途經那條最熱鬧的街,掀開不知名布料織成的精美車簾,似乎能看見萬千個她的希冀寫在臉上。
或許昨日死在溪邊的魚,今日轉投了人道,難道是她修持了五戒而天降神跡嗎?
懵懵懂懂地下了車,仕女們攙扶著她進殿,雖然聖女盡量和她講得詳細,但即便如此,這座華麗宮殿對她而言,仍是十分陌生。
為了避免露餡,她沐浴過後就一人待在寢殿,消化今日所發生的事。
就像夢一般,一個好得不真實的夢,錦衣玉食,不必為一餐一飯所苦,不必任人欺凌。
她穿著絲綢做的寢衣,至梳妝台前落座,一舉一動都小心翼翼,彷彿動作大了,美夢就會被驚醒。
鏡子裡的人不像她。
不知是不是鏡子扭曲了她的面容,又或者人要衣裝,佛要金裝,她與聖女的差別,是不是只在那一身衣服而已?
突然她想起聖女對她說的:「作為聖女,你這輩子將再也無法嫁人生子,雖道女為悅己者容,但沒有人可以比你更愛你,你明白嗎?」
早在她破瓜時,她就沒了要嫁人生子的想法,一介孤女,無依無靠,還沒了身子,誰會願意娶她呢?
從那之後她再不願梳妝打扮自己,但如今,聖女卻和她說,她能夠只為了自己打扮,因為這世間最愛她的人便是自己。
那一刻她又想起了進到聖殿之前的心情:她與聖女相比,是如此骯髒卑微。
她無法理解,為什麼聖女要和她交換身分,卻仍懷著私心答應了這樁交易,給了聖女所謂的自由,讓她放棄了這樣衣食無缺的環境,去換備受欺辱的生活。
昨日之事,她不過一個晚上就能夠當作新生,全因這是她作為一條魚,時常要迎來的風浪,但若是換作聖女……
即便聖女說了只待個幾天,但誰又能保證這幾天那群惡棍不會找上門來呢?
愁腸九轉,偷來的日子安穩卻不舒心,明明入口是玉盤珍饈,卻味同嚼蠟。
她安享著聖女的好,把人推向了火坑,愧疚到了極點,張口卻撒謊自己過得很快樂,她與聖女的差別,又何止是幾件華美的衣裳?
—
經歷連兩日的祭祀,聖女面上倦色難以遮掩,揹著事先準備好的小包袱就坐上安排好的馬車回到小村中。
自小生活在深宮中,莫名其妙被選上作為聖女,她從未一個人在街上走動過,這陌生而貧脊的地方,卻如林間能讓她這隻被馴養久了鳥兒自在鳴啼。
她準備得不算萬全,除了一點銀錢與樸素衣裳,就無他物在身,出逃之事她自知不會被追究,只因那群王公貴族壓根就不在乎聖女是誰,只怕若傳出丟了聖女,反而動搖民心。
天色向晚,但是村中的市集依舊熱鬧,她餓了一天,又初獲自由,便往人群中走去。
打量她的目光如密網,雖然與女孩換的一身衣服實在簡陋,卻掩不住她自幼在宮中成長的貴氣。
但她早已習慣了眾人的注視,並不在意這些無形的目光,如同在水下憋氣久了的人,終於能夠上岸,便只能不管不顧地大口呼吸。
為了活下去,哪還顧忌別人的眼光。
她找了間麵食館吃了晚餐,是她不習慣的味道,可她還是一點不剩地吃完了,雖然白日裡與女孩承諾不必擔心她,實際上,她也不知用光了銀錢該怎麼辦。
她十歲便被選為聖女,在那之前也是家裡嬌養的貴女,雜務從來輪不到她來做,就連女紅也是差強人意,又要怎麼和女孩一樣給人做活來養自己呢?
即便想清楚了這些,她還是逃了,好不容易才看見陽光,若又要跌入黑暗,那恐怕她的一生,都將進入永夜。
回到廢棄倉庫的路上有些曲折,雖然按著女孩所說的去找,卻找不到她所謂的家在哪。
「喲!你在這啊?」粗嘎的男聲在暗夜中響起,一聽就來者不善,她腳步未停,只怕是什麼地痞流氓,又怕是女孩的舊識,馬上就打照面很快就會漏餡。
「你跑什麼!」倉促的腳步聲追在背後,聽起來只有一人,她在小巷裡透出窗戶紙的明滅燭光中奔跑,過了轉角入眼就是女孩所說的倉庫,眼尖看見倉庫外放的木柴,撲將過去。
手掌擦破在木頭上,有尖銳的刺痛感在掌心,但她仍然雙手抓起劈好的柴木作防禦姿態。
她頭一次面對這樣的場面,腦海裡只有一個想法,連痛覺因此被淡化:「我已經自由了,沒有人能夠欺辱我。」
大概是她眼裡的決絕太過強烈,追來的男子竟有些被震住,回過神後,隨即諷刺道:「怎麼,又要學上次拿石頭砸人嗎?昨天的教訓還不夠?還是說……」
給足了的停頓像是要給她最後的痛擊,她隱隱猜到了什麼,腦袋有些發昏,似甫上岸呼吸,就又被人壓著腦袋沉入水中:「你還想再試一次?也對,我看你後來也叫得挺開心不是嗎?哈哈哈哈!」
刺骨的冰冷漫上周身,她徹底沉入水底。
—
「聖女殿下,宗伯請您去宮中的聖殿。」侍女躬身在寢殿門口通報時,她正一人坐在梳妝台前拆解頭上的首飾,早已是入睡的時間,這莫名的宗伯卻來找她。
聖女要她這幾天都別見宮裡的人,怕會漏餡,便問道:「能拒絕嗎?」
侍女明顯有些為難:「這……您已經七天沒有見人了……」
外頭一點光也無,夏夜的雨撲打著窗,砰砰作響,像是她的心跳:「就、就說我已經睡了!」
為什麼要這時候來找她呢?鏡子裡的她不安上了眉頭,這幾日竊據榮華富貴的沉重在此刻達到了高峰。
「哈哈哈!還在生我的氣?」忽然侍女叫了聲宗伯,寢殿的珠簾因被掀開而叮噹作響,她嚇得回頭一看,略有福態的男子大步跨了進來,看見她,打住腳步打量了一番。
他是誰?難道是聖女的父親?她咬著唇按捺恐懼,強迫自己冷靜思考:她記不得聖女與她說過的官名,卻知道絕不是這個所謂的宗伯。
那為何這個宗伯會在晚上闖入一名聖女的寢殿?她有些不敢繼續往下想,但臉上早已一片慘白,偷眼去瞧寢殿之外,侍女都消失了蹤影。
「怎麼啦?幾天不見就認不得我?都說了上次是意外,半年一次的聖祭,那群人不知手腳輕重,難免有些興奮過了頭嘛。我和你保證,這次不會了!」
宗伯眼裡的情緒她太過熟悉,像是當頭一棒,打得她頭疼欲裂,她不太想聽懂,卻每個字都清晰地傳入她耳裡。
明明是黑夜,她卻恍然見到了那天毒辣的太陽,隨著伸過來的雙手,灼得她疼痛。
寢殿裡的燭火搖晃,仰著頭,她想:她終於理解了為何聖女要逃出宮。
她們都欺瞞了彼此,但她恨嗎?大概只剩為自己與聖女的同情與愧疚。
村裡的大嬸們都知道她過著怎麼樣的生活,或要她逆來順受,或要她像上次那般舉起石頭,卻總沒有人為她搬開那些壓在她身上的沉重。
她以為換上了錦衣華服,就能過上她想要的生活,但從前那些委屈卻從來沒有消失過,所有情緒都沒了出口,只能堵在胸中鬱結地令人作嘔。
在將她靈魂抖落的震盪中,她才想起,五道謂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、不邪淫,但她卻犯了邪淫之罪,莫怪她這條小魚無法超脫畜生道。
天亮了,小高臺上能看見雲與魚肚白的天融為一色,雨夜沖刷土壤成了濕潤的暗紅色,她流淌在泥裡,像是回到了最原本的她。
—
她住進了女孩原本的家,前幾日追著她的人不知為何走了,她卻因而發覺,這世間就是地獄。
做了多年的神靈代言人,卻從沒聽見過神的聲音,她放棄了向神祈求救贖,這日日夜夜卻在輾轉難眠的夜裡,向神傾訴己身罪過。
這聖女的名頭掛在她身上,一點也沒讓她變得聖潔,至今她才為自己犯下的罪孽愧疚、失措。
幾天的反省,讓她領悟,她以為的沉入水底,腳下還踩著他人的屍體,就連入水前灌入她鼻中的一點空氣,都是因為踐踏別人才得以呼吸。
原本她只想在這裡住幾天,就找個新的住所重新開始,如今卻突然不知該何去何從。
她不知道這是不是她想要的自由。
經典裡告訴她應該如何取悅神靈,卻沒有告訴她如何取悅自己,她還深陷在巨大的悲哀裡,這一份苦楚,似乎充斥這不公平的世間,無論怎麼逃,也無法逃出生天。
喧鬧的聲音從薄薄的木板門外傳入,幾個陌生男孩闖了進來,這一次她卻再也沒有勇氣去對抗,就像以往無數次的祭典。
「到處都敲了鐘,說聖女回天了,這種時候肯定不會有人注意到的。」不知道哪個人笑著說了句,如那支鐘杵敲擊的是她的心臟,她瞪大了眼。
「聖女、聖女回天……」喪鐘似是敲在她耳邊,頭暈目眩。
「哈哈哈哈還回天呢,誰不知道就是死透了的意思!」幾個人都笑了起來,粗嘎的笑聲像是送聖女最後一程的輓歌。
她突然出手對那群男孩拳打腳踢。
「這瘋婆子!」「架住她!」
視線逐漸模糊,她的神魂沉在水底,世界隨著空氣的抽離變得安靜,恍惚中彷彿看見了女孩與她一起。
她的身升至高處,低垂著頭,像是以往高坐上首的聖女,舌吐在外頭,卻嘗不出幸福。
她想,或許是她吃光了這榮華富貴的蜜糖,糖心是鋒利的刀片,待她醒悟、逃出,整條舌頭都已鮮血淋漓,再難以體會世間味塵。
‧ 原創小說,轉載請詢問並註明出處,侵權必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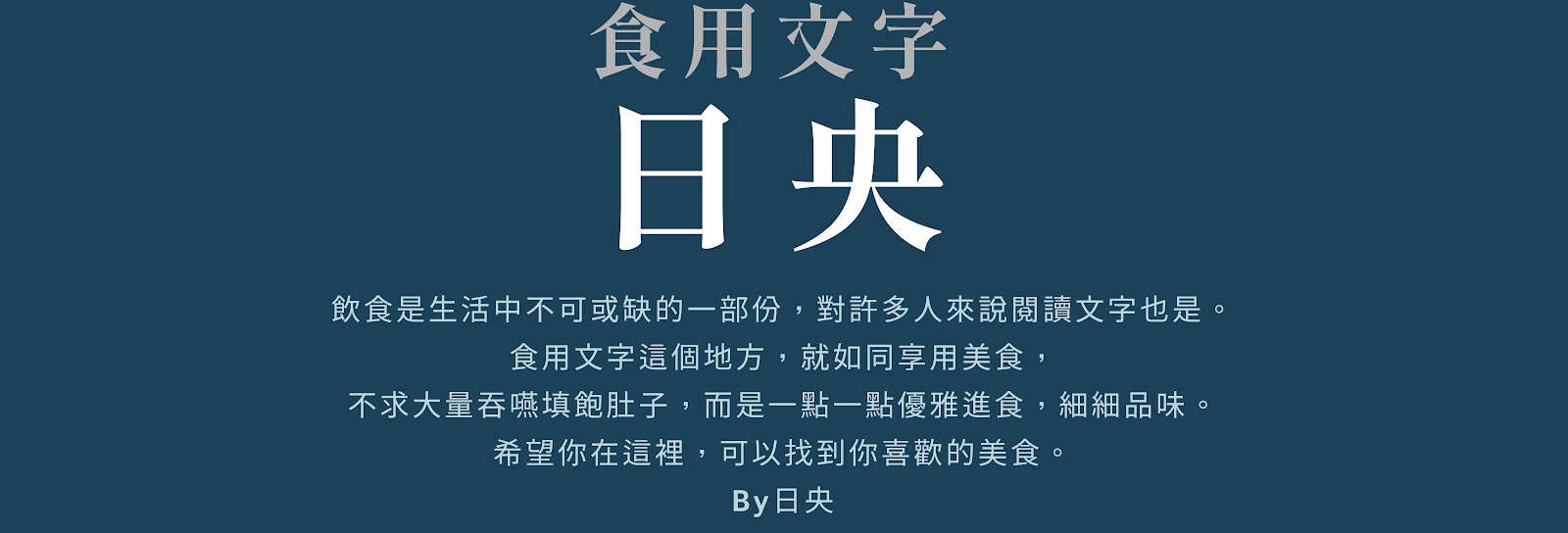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
張貼留言
留言需經審核,謝謝大家的等待。